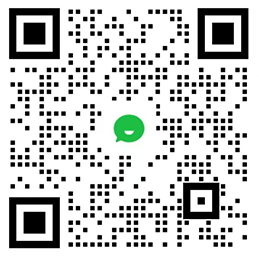江苏/连云港-2024-12-30 00:00:00
【品味海州】石湫堰
“石湫堰”今人知之者甚少,但它在历史上却小有名气。仅在《嘉庆直隶海州志》中,就出现多达**余处;而在《续资治通鉴》《宋史》等史料上,也多有记述。如《宋史·李全传》:“李全与金人战于高桥,不胜退守石湫”;《续资治通鉴》:“金人数万众围海州。诏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往援……,子盖整军渡江,取涟水至石湫堰”等,可见一斑。因其在历史上具有特殊位置,近代人谭其骧先生编著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宋金元卷》中,在二百四十五分之一的地图上,于今之锦屏山南麓的相对位置处,也特别标注出石湫堰。
石湫堰在海州的历史上,是集农田水利、交通要路、军事关隘于一体的复合性建筑设施。它对今人研究古海州的水利、交通、军事,尤其是海州抗金战事,无不是一重要的史料。又由于历史的变迁、海水的推移,及近代农田水利的整治,石湫堰今已不复存在。但据笔者近十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,基本上搞清了其相对位置。即:其南起于今新坝至大穆村间,向北沿昔日的海沭路间,至八一河后转向东,至哑叭山东南麓折向北,直至和今日朐山村——锦屏镇公路接头处。
海州志还记述有石湫堰一直延伸到孔望山下一事,志书中时有称石湫堰为石闼堰者,两者是否是同指一物?故留待下面一并分析阐述之。
一、石湫堰的作用与其建筑年代
“堰”者,为堵水的土堤。按当地风俗称“堰”者,一面有水的只称堤或坝,两面有水的堤或坝,才习惯称堰。
在海州志中,称堰的有:西捍海堰、东捍海堰、大村堰、王公堰、南堰、沙堰,及近代的太平堰和黄九堰等,而又无一不是在水中穿行。
海州地处海陬,其筑堰的目的,是外遏咸潮,内蓄淡水,以卫农田。当堰处于交通要道处时,堰除可阻海潮浸漫外,亦利商贾行人。而石湫堰建成后,也正收到了这两种效果。另外,在石湫堰极盛时期,其东是浊浪滔天的黄海,其西是由沂沭两河蓄成的泱泱泽国,而堰由其间穿过,隐然有城堑之险。因此在宋元时,海州人民据此拒敌,曾谱写出一曲曲抗金的壮歌,自今尚被人民所传颂。如《宋史·魏胜传》:“宋绍兴三十一年,(金人)复发诸路兵二十万来攻海州,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饷道,胜择勇悍士三千余骑拒于石闼堰,金兵不能进,逮夜始还,留千人备险隘。金兵十万来夺,胜率鏖战,杀数千人,余皆遁去,下令守险勿追。”魏胜于此处之所以能以少胜多,勇挫金兵,其主要是仰仗石湫堰之险也。故石湫堰在战争年代又有着关隘之功能。
宋时的海州治朐山县(今孔望山下),其东是海,其北是海,东南是海,西北也是海。有朋自远方来,无论从鲁东南、豫皖、或苏南,只要走陆路,必经石湫堰至海州。故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载:“石曼卿通判海州,故人布衣刘潜访之,迎于石闼堰。”
我们从下面一段文字再来分析证明,宋时石湫堰的交通作用及其所处的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。《宋史·李全传》:“宋李全与金人战于高桥,不胜,退守石湫。”高桥,南宋时地名,在今岗埠农场去赣榆墩尚的途中位置。至清嘉庆海州志脱稿时,尚注明高桥是通赣榆县路。而李全曾为农民义军领袖,归顺宋时为忠义军,后官至南宋淮南东路总管,辖地为今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兼经略鲁南一带,今之海州师范是其旧宅也。在这儿“李主……于高桥……退守石湫。”可以理解为,李全原驻守石湫,因与金人战而去高桥;不胜后,走原路退返石湫防守。可见石湫堰在南宋抗金年代里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;同时也证明昔时鲁东南地区去海州或去苏南地区的陆路,石湫堰则是必经之路。
试想,在石湫堰北首哑叭山巅,如派有军队驻此了望,凭其据高临下之优势,既使在十里之外行进在石湫堰上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、车骑兵马,也可以一览无余。而紧排着哑叭山东麓的石湫堰路段处,一边是海,一边是山,是进出海州的咽喉要道,这又形成了海州的天然门户。拥兵驻此,大有一夫当头,万夫莫开之势。今人在此处路旁的农田内,曾发现一块经人工凿有擅子的巨石,判断其为昔日的闸口用石。笔者则认为,它是当时守军白天升降大旗,夜间悬挂灯笼等物以示方位,而使用的固定旗杆类形的基石;抑或这类旗杆类的设施,其本身就是城池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建置模式。
石湫堰建于何时?目前尚未见有史料记载,不敢臆断。但在《宋史·河渠志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:“宋天禧四年(公元****年)淮南劝农使王贯之,导海州石闼堰水入涟水军以溉民田”。文中涟水军之“军”字,是南宋时的政区建置的一种称谓,相当于县,即今之涟水县。这段文字不仅证明了石湫堰之水有灌溉民田的功能,还证明其水尚可恩泽到七十里开外的涟水县之功效;同时又从另一角度道出了在公元****年前石湫堰就已存在这一事实。
其实,上面所提及到的:西捍海堰,南北长六十三里,造于隋开皇九年(公元***年);东捍海堰,长三十九里,造于隋开皇十五年(公元***年),它们均比宋天禧四年要早四百多年。可见海州的先民们在筑堰阻水,以利良田等水利设施方面,早就有此举措。因此,石湫堰筑于宋天禧四年前,就不足为怪了。但其建筑的具体年限可以上溯到何时?只得留待日后去探讨了。
但“石闼堰”这一称谓,早在公元前***—**年间汉武帝在位时就已有了。只可惜它是另有所指,而非海州的石闼堰。但不排除海州的石湫堰因受其影响而又称石闼堰这一可能性。故笔者将此相关的一些文字摘抄为下,供参考,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:“石闼堰,在陕西长安县西南。《水经注》交水西至石堨,汉武帝穿昆明池所造。《通监(金旁)注》武帝作石闼堰,堰交水为昆明池。唐太和后,堰废而昆明涸,今其地名鹳鹊庄。”
二、千年遗址今何在,黄河夺淮寻踪迹
公元****年,靖康元年,金兵攻破京师(今河南开封市),虏走宋朝皇帝徽、钦二宗,金帅立张邦昌为楚帝。史家称其为“靖康之耻”。
公元****年五月,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(今河南商丘南),改元建炎,是为高宗,南宋始此。高宗召主战派李纲为相,李纲荐宗泽任知开封府,东京留守。八月,李纲受黄潜善、汪伯彦排挤而罢相,在位仅七十五天。九月,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岳飞等七千人渡河抗金,旋即失利,王彦奔太行山结营,部下刺“赤心报国,誓杀金贼”八字于面,号“八字军”。时两河民兵纷起抗金,各部多附王彦。十月,宋高宗南迁扬州。
公元****年,建炎二年七月宗泽忧愤而死,杜充继任东京留守。十一月,杜充于李固渡(今河南滑县西南)西决黄河入清河,以阻金兵,黄河自此不复故道。决河由泗(南清河)入淮河,会淮水后入海,是为黄河河道南移之始,史家称此为“黄河夺淮”。
黄河夺淮时间长达***年之久,直至清咸丰六年(****年)黄河才又改回故道,由山东入海。
在黄河夺准期间,黄河因带有大量泥沙,使淮河河床逐年增高,屡筑屡决,其间给苏北、鲁南、豫东、皖北等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,黄河有段时期甚至改道由今之灌河口分流入海。又由于黄河的大量泥沙流入黄海,使宋时尚地处海边的今之盐城、阜宁、滨海、响水、灌云等地的海岸线,向东推进了*****公里不等。同时也使昔日位于海中的云台山于康熙**年(****年)与陆地相连。
当然,海岸线向东推移的原因有多种,但黄河带来的大量黄土泥沙沉积海底,使海底增高也是其主要原因。
笔者曾于****年间,在南城西山西麓、新浦至灌云公路东侧,即云台棉麻加工厂厂址内,进行地质探方时测得黄土沉淀层近一米厚度。又于锦屏镇普安村东约*.*公里的新坝二砖厂内,在采土烧砖用的土坑中,测得黄土沉淀层均在一米以上不等。
石湫堰筑于北宋天禧四年前(****年),而黄河夺淮则晚于南宋建炎二年后(****年),故石湫堰阻淡水的一边不会有黄土,而阻海水的一边则必有黄土沉淀层;黄土越接近堰边,沉淀层就越小。
笔者于是遵循这一规律,往返于石湫堰址两侧进行多次实地考察。当基本摸清石湫堰的相对位置后,又曾多达数十次地进行实地挖掘与采访,也曾得到数十位热心人的帮助,使考察进程得以加快,并能更接近于实际。为此,笔者十分感激他们。然而,最使笔者难忘的则是在****年大年初二,在周庄南有几户农家,其时正合家团聚喜乐融融时,笔者这位不速之客突然撞入,其家人不但不怪罪,还热情地敬烟、端茶,甚至要倒酒……当笔者说明来意后,他们倾其所知,尽情相告;这一带解放前都是盐碱地,经过解放后多年的挖沟淡碱,施肥翻整,才慢慢地种出庄稼来;他家的宅基下,黄土还有一锹多深(约*******)。后又指派一位**多岁的壮年人,陪笔者到海沭路沟旧址一带进行实地考证,并告之,昔日“袁饭棚”的确切位置和具体用途,以及一些历史变迁和社会掌故,使笔者得益非浅。可惜时隔七、八年,这位农家的姓氏已忘却,为表示谢意,权将这篇文章献给他们全家,尚不知他们能看到否?
石湫堰的遗址已基本弄清,即今日之具体位置是:南起于新坝镇政府向西去大穆村路中约一公里处的今之电灌站,向北经谢圩、张桥、夏庄西、袁庄东、至八一河处折向东;经前店、至张庄东偏南向,再转向北偏东向,沿刘志洲山东麓今之乡间公路,到岗嘴村西侧和朐山去锦屏镇政府的公路交接处:此处亦为石湫堰之北端。为便于下面阐述,笔者将上面所述的这段遗址,暂称之为古石湫堰。
在张庄东,即哑吧山东麓至岗嘴村这段古址——今乡间公路路基两侧,有一怪异特征:沿刘志洲山东麓的这段公路两侧,理应西高东低,或者两侧持平,但在实际考察中,路东地平却有一段明显地高出路面。在究其原委后,更进一步证实了,这儿正是古石湫堰堰址。因为黄河夺淮后,在长达***多年的岁月里,是海水无法越过到堰西,黄土只能在堰东,经长期沉淀堆积后,而逐渐形成的。
三、石湫堰的旁支及延续
关于石湫堰一直抵达孔望山下之说。笔者的理解为:在元以前,海州治朐山县的历史很长,而古石湫堰又始终是进出海州陆路的唯一重要通道,即使到了清末民初年间,海州虽早已迁至今日之海州城内近八百年,但这条路却依然发挥其主要作用。因此,在孔望山至岗嘴一段的道路,借助于昔日的诸多银山坝类的防海堤坝的建筑,加固加宽和古石湫堰连成一体。尤其在南宋抗金频繁时期,从战争的军事需要出发,为防金兵大军压境,充分调动守军的战斗力,以利步骑快速增援,这种加固加宽更显其必要。天长日久,人们习惯地将这段堤坝类公路,一并称之为石湫堰,也属情里中来。按《嘉庆海州志》引《陈志》孔望山条目下曰:“南宋开石湫堰,戍守於此”,就是最好的注脚。但这段堤坝,绝非是古石湫堰也。
另外,石闼堰与石湫堰之说,是否确指一物?笔者则认为是另有所指。因为筑石湫堰的主要用途,是阻鲁南等地的沂沭之水南泄。而上所述的古石湫堰由南向北,至八一河处则已经向东去;因之,就敞开了八一河向北至刘顶方位的一个大缺口。而沂沭之水又正由此经过向南,这自然是先民们搞水利时所不取的。故这儿必筑有一堰或为一坝,并与石湫堰相连接,但因其建筑时间不同,或因使用材料不同(如石头),故另名之为石闼堰以示区别,抑或是借用汉武帝所筑之堰名,亦未不可。
总之,这条堰(堤)是存在的,其孰先孰后,仍是一个谜,但它早于其南部的石湫堰可能性很大。而上面所提到的“李全与金人战于高桥”,正是由此进出的。因此,对于石湫堰这一整体而言,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;对于后人或外地人来说,时而称石湫堰,时而称石闼堰,应无大错。犹为今之赣榆人在外地,谈起家乡时,或曰连云港市、或曰赣榆县,是一样无可指责的。
四、千年石湫成土丘
(一)由于黄河夺淮后大量黄土泥沙的沉积,加之顺治十八年的裁海,和康熙七年的郯庐地震等诸多地壳运动因素的影响,使海州地区海岸线东移。因之在石湫堰外侧的海水也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波涛,慢慢地露出了大片滩涂,只有在潮汛大时,才会偶然地涌及到堰边。先民们为围海造田,在清乾嘉年间,距大穆至八一河段的石湫堰东侧约*.***公里的不等位置,重新筑了一条新坝以阻咸潮。其走向大约为,今之新坝镇向东北方、经旧民航机场东、至哑叭山东麓与古石湫堰衔接。于是就又出现了在新筑坝基西至古石湫堰东侧的一片地区,黄土沉积较新坝基东的一片地区则少了一百五十年的沉积层。
(二)由于新坝的筑成,南来北往的部分商旅行人,尤其是去海州的商客,则被其分流过去相当部分。因此,古石湫堰也渐渐地失去昔日的繁忙和军事关隘的险要。到了清末,古石湫堰在交通方面的功能,已基本上被新坝这条路所取代。君不见海州巨宦沈云沛于****年病逝于天津后,其灵柩正是从海州东门进来的;为了安葬于锦屏山南麓,又从东门出殡,这正犯了丧家之大忌,而又不得不为之;究其所以然,走锦屏山东路是正道,走山西路则为旁道,昔日之旁道,实实崎岖难行也,故为沈家所不取。
(三)石湫堰在海州的历史上是交通、水利、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最好的见证物。可惜历经千年沧桑,今已不复存在;虽曾残留下一点遗址,经过解放后大面积的水利兴建和农田改造,则更难觅踪迹,即使今日掘地三尺,昔日的黄土也难得一见。然而,事物有其必然的一面,也会有其偶然的一面。石湫堰在大兴农田改造的年代里,于两村或两镇间的分界点,或因谦让之故;或为丈量工程土方用;或怕挖过了界,而伤彼此情份;故残留下一小段遗址。其状若荒丘,杂树丛生,高高地隆起于田间。夕阳西下,余辉残照在上面,身后落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。当笔者第一眼看到它时,心中说不出是惊喜还是悲凉。世上的文明与进步,都是以破坏旧的为基础的。犹如今日研究妇女解放的学者们,因看不到旧时女人的三寸金莲,就抱怨废除了缠足制度一样,于是我也就释然了。
在清乾嘉年间修筑的新坝,同样也得到了如此的“礼遇”。但今日依稀尚能看到一点痕迹,因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,在此就不再赘述了。
上面拉拉杂杂地写了一点与石湫堰相关的文字,谈不上研究,算是一点心得体会吧,必有谬误之处,望能得到方家里手的批评指正。
来源:海州文史资料第五辑